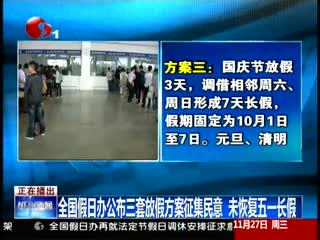總有一天我們會發(fā)現(xiàn),“互害”這兩個字不算過份地描述出了我們的現(xiàn)狀。發(fā)生在食品安全領(lǐng)域種種無底線的潰敗,已經(jīng)為我們提供了鮮活的例證。比如最近短短幾天里,“病死豬”、“老鼠肉”、“‘毒藥姜”等問題農(nóng)副產(chǎn)品接連被曝光。而以“毒藥姜”為例,山東濰坊有些姜農(nóng)使用“神農(nóng)丹”種姜,神農(nóng)丹主要成分是一種叫涕滅威的劇毒農(nóng)藥,50毫克就可致一個50公斤重的人死亡。
不出所料的是,“毒藥姜”的種植者表示,“我們自己吃的姜不使這種藥,另外再種一溝”。許多食品生產(chǎn)者不肯食用自己的產(chǎn)品,大抵已是一個普遍的規(guī)律。當河南新鄉(xiāng)一家造紙廠附近的農(nóng)民說,“地里產(chǎn)的糧食都賣了,我們自己都不敢吃。”福建福鼎市某村的農(nóng)民也表示“我們都不敢吃自己種出來的大米了。”而當某致癌金針菇生產(chǎn)企業(yè)坦言“自己生產(chǎn)的,自己一般不吃”之時,某知名飲料廠也被曝員工從不喝自己生產(chǎn)的飲料。但是,為何當許多人都努力使自己免于被傷害時,卻又總是一再地成為那個害人者?
在這種情形下,那個自稱為“無良農(nóng)民”的徐清元的出現(xiàn),是有意義的。這個據(jù)說曾經(jīng)生產(chǎn)毒產(chǎn)品而后改邪歸正的農(nóng)民表示,“賣假奶粉的絕不會給兒女吃假奶粉,但他能保證不吃我的毒白菜嗎?賣假酒的能保證不吃毒肉嗎?養(yǎng)雞賣飼料的能保證不喝假酒嗎?你覺得你占了便宜,我覺得我占了便宜,最后大家同歸于盡。”事隔多年,我已經(jīng)沒辦法找到關(guān)于徐清元說法的出處,以至于懷疑他是不是一種杜撰,但這已不重要。重要的是,這樣一句流傳甚廣的話的確指出了一個互害型社會的實質(zhì):當我們本身作為施害者而存在,最終沒有誰能免于被傷害。
我注意到,一些公共事件發(fā)生后,我們總是很容易地找到政府部門以及體制性原因。這固然沒錯,但誰能說,在政府及公權(quán)力之外,同樣處于社會架構(gòu)重要一端的民間社會及公民個人,沒有一些更值得關(guān)注的問題?但是一直以來,我們常常會主動避免將過錯指向蕓蕓眾生。正像一說到中國人,就難免定性為勤勞、勇敢、善良一樣。但不論是回避,還是空洞定性,其實都包含了許多讓人不以為然的自欺欺人。社會學(xué)家孫立平在觀察黑磚窯事件時發(fā)現(xiàn),弱者對弱者的殘害,可能會達到一種更殘忍的地步。他由此得出的“窮人禍害窮人”結(jié)論,亦正是一種“互害”。
沒有人是一座孤島。在一個“互害”社會里,同樣沒有人能置身事外。不論是食品安全,還是建筑質(zhì)量,不論是山西的黑磚窯,還是佛山的小悅悅,不論是安元鼎事件,還是各種環(huán)境事件,互害型社會所展示的尊嚴感以及安全感缺失,無疑是整個社會道德淪喪的一種反映。于是,我們就這樣生活在一個多么奇特的時代場景之中:每一個人都不可避免地成為受傷害者時,每一個人也不由自主地在成為那個作惡者。我們一邊對于道德淪喪的狀況感同身受并深惡痛絕,一邊卻又常常變成自己所痛恨的那種人。這到底是國民劣根性所在,還是一種醬缸文化的繼續(xù)?
一個社會的道德現(xiàn)狀,絕不是一件與我們大多數(shù)人無關(guān)的事情。如果說社會道德淪喪,那么又是誰構(gòu)成了這個社會?而當我們每一個人都開始抱怨社會道德已經(jīng)嚴重淪喪之時,我們每一個人本身,難道不同樣是它的參與或推動者嗎?這不是可以埋住鴕鳥頭的沙子。不論是向更弱者抽刀,向更強者獻媚;不論是更多地孰視無睹或同流合污,還是種種向不確定的社會公眾輸出一些不以為意的惡;不論是欣欣然擁抱社會道德的狀況如魚得水,還是在假裝落寞之余以道德的現(xiàn)狀作為自甘墮落的理由,其實最終在加劇社會“互害”的程度,也在進一步惡化我們的道德生存環(huán)境。
我們最終需要有徐清元式的覺醒與悔悟,最終需要從“互害”式社會中走出來。在這之中,不僅需要少一些受害者心理,更應(yīng)少一些報復(fù)社會的心理。勿以惡小而為之,勿以善小而不為,與此同時,勿以社會道德淪喪來作為個人缺德的理由,勿以體制問題作為我們逃避公民責任的借口。人人守底線,社會才會有底線。除此之外,任何對于道德現(xiàn)狀的順從,對于公民責任的規(guī)避,都不可能使社會實現(xiàn)有建設(shè)性的道德重建。良好的社會道德,亦即公民社會目標之所在。而所謂公民社會的培養(yǎng)與發(fā)育,不就是一個政府組織與民間社會共同成長的過程嗎?

 分享到人人
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
分享到QQ空間










 恭喜你,發(fā)表成功!
恭喜你,發(fā)表成功!

 !
!